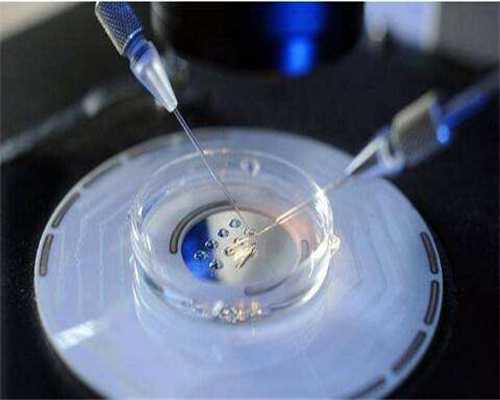抗战胜利77周年之际,登记在册的“慰安妇”幸存者还剩多少位
苏智良的历史研究,看上去一个比一个“剑走偏锋”,却一次次赢得瞩目、钦佩。
苏智良的另一个研究对象更让人犯怵——黑社会。在近代上海城市,黑社会一度猖獗。“我希望通过自己的研究,让大家看到黑社会组织是怎样形成和壮大的,有没有什么教训可以借鉴,从而让全社会保持足够的警惕。”
在苏智良的办公室里,有几幅醒目的电子地图展板。每一个红点,都是他和团队成员用脚走出的红色遗址。
经过10年的调查与走访,苏智良及其团队于2020年推出《初心之地——上海红色革命纪念地全纪录》,上海红色革命文化旧址、遗址一举增加至1000处。
相对于耳熟能详的中共“一大”“二大”会址来说,新考订的近400处红色景观包括中央特科联络点、上海地下党秘密钱庄、中共协助建立的二战南市安全区等,更加完整地展现了与革命相关的名人故居、民主党派人士在沪活动点,以及与革命事件相关的印刷所、出版社、书店、电台、难民收容所等。
2022年,苏智良来到上海长治路177号,确认这里是上海俄文生活报馆、共产国际东亚书记处、维经斯基的工作地点。在这里,陈独秀与维经斯基探讨中共建党,毛泽东增进了对十月革命的了解。
在城市史、革命史研究之外,苏智良最花气力、最为人所知的无疑是“慰安妇”问题研究。
30年来,从繁华都市到黎村苗寨,苏智良及其团队数十次赴全国各地调研,通过实地走访、聆听受害者口述、查阅地方志等建立研究档案。
没有比挖掘自己民族受辱历史更为残酷的事了。而之所以坚持调查,是为了拒绝遗忘。
当苏智良遭遇不理解、不配合乃至不支持时,他获得了妻子陈丽菲的鼎力支持。
陈丽菲一开始是反对丈夫研究“慰安妇”问题的。但1996年,在协助翻译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对“慰安妇”问题的调查报告之后,她改变了想法。“我们没能在国际上提供有力的调查和研究证据,没能为自己的民族说话。因为我们的历史缺失了。”于是,陈丽菲毅然推掉了其他的科研工作,协助丈夫开展工作。
2000年,苏智良、陈丽菲走进秉塞大山深处,探访云南地区唯一一位愿意站出来揭露当年日军暴行的幸存者李连春。在深夜的火塘边,老人对陈丽菲说:“我很穷,但我有最宝贵的东西,就是我自己的身体,多少钱也赔不来。我不是要钱,也不要找谁报复。我就是为了要世间的公道。”
闪闪的火苗,映照在老人因常年流泪而白翳重重的双目里。
1999年,苏智良创立中国“慰安妇”问题研究中心,开始在全国范围内援助“慰安妇”幸存者群体。2000年,在学校的支持下,苏智良及其团队协助设立“慰安妇”研究与援助项目基金,进一步加大对幸存者的生活、医疗和丧葬援助。
许多上海市民获悉此事后,纷纷伸出援助之手。一对普通的退休夫妇徐修国和曹慧缇,多年来共捐款48万元。
岁月留痕,正义有声。在“慰安妇”幸存者生活不断得到改善之时,相关历史记忆保护工作也在稳步推进。
2014年6月,南京利济巷慰安所旧址陈列馆揭牌,苏智良任首任馆长。这座规模庞大、保存完整的慰安所旧址,现已成为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分馆。
2016年10月,中国“慰安妇”历史博物馆在上海师范大学落成。不远处,一组由中韩艺术家无偿捐献的“慰安妇”和平少女像安坐在椅子上,长久地凝视着眼前的土地……
「少女像背后,是全国各地幸存者的脚印」
上观新闻:在上师大人文学院的草坪上,有一组“慰安妇”和平少女像。一位中国少女和一位韩国少女坐在椅子上,衣领被拉开。她们双手握拳,神情悲愤。身旁,还有一把空椅子。这把椅子为什么是空着的?
苏智良:这是韩国雕塑家的创意,表明“慰安妇”的受害者不只是中韩两国妇女。同时,参观者也可以坐下来,与少女“对话”。
上观新闻:少女像后面还有一串脚印,又意味着什么?
苏智良:我们志愿者为数十位幸存的“慰安妇”老人保存了脚模。少女像后面的脚印便是这些全国各地幸存者的脚印。现在老人们大多已经去世了,但这些足迹将永远留存。
上观新闻:在上师大内的中国“慰安妇”历史博物馆里,有哪些重要收藏?
比如,“慰安妇”幸存者捐献的各类纪念文物中,有万爱花赴日起诉时使用的护照、袁竹林到海外出席听证会的证件、雷桂英从南京高台坡慰安所带出来的高锰酸钾和她的临终遗嘱,还有林爱兰作为“红色娘子军”一员获得的抗战60周年纪念章以及她日常行医的用具,等等。
我们希望,来博物馆参观的人,可以接受一次深刻的历史教育、和平教育。日本法西斯利用国家政权力量,把大量女性作为性奴隶使用,这在世界文明史上是空前的,是法西斯对世界文明的侵害,我们不能忘记。
「中国“慰安妇”人数最多、遭遇最惨」
上观新闻:根据您的调研,二战时期到底有多少女性遭受到日军“慰安妇”制度的戕害?
中国是日本法西斯“慰安妇”制度的最大实施地,是日军设立慰安所最多的占领地,中国“慰安妇”人数最多、遭遇最惨。我们的统计显示,1931年至1945年间,日军强征掳掠了20万以上的中国妇女作为性奴隶。
上观新闻:在世的“慰安妇”幸存者,还有多少位?她们的近况如何?
苏智良:截至目前,中国“慰安妇”问题研究中心登记在册的中国大陆地区幸存者仅剩下12位。她们分布在湖南、山西和海南,年龄大多在九旬以上。她们大多身缠疾病、无儿无女,好在现在基本生活都有了一定的社会保障支持。
虽然不清楚自己还有能力做多少事,但有两件事我会一直坚持下去:一是继续援助健在的幸存者,哪怕是微薄的;二是会将“慰安妇”问题调查下去,将新增的、零星的线索一一落实。
1997年,苏智良、陈丽菲在崇明岛探望幸存者陆秀珍老人。
「他决定延迟一年回国,查找一手资料」
上观新闻:2022年8月14日,是第10个世界“慰安妇”纪念日。这个纪念日为何定在8月14日?
苏智良:1991年8月14日,67岁的韩国妇女金学顺在沉默近50年后,首次公开站出来向世人表明自己被迫在中国做过日军“慰安妇”。从此,被日本政府刻意隐瞒的军事性奴隶制度终于被揭发。这是8月14日成为世界“慰安妇”纪念日的主要原因。
上观新闻:那个时候,您正在日本访学?
苏智良:是的。1991年12月6日,金学顺等3位韩国妇女走进日本东京地方法院,起诉日本政府,指控日军对她们犯下的性暴力罪行。当时,我正在东京大学做客座研究员,目睹了金学顺老人的示威游行。
之后,一个日本教授在国际会议上问我:日军的第一家慰安所是不是在上海?我一下子被问住了。于是,我决定延迟一年回国,查找关于中国“慰安妇”的一手资料。
最终,我在日本的一家旧书店里发现了一张黑白照片:上面是两排日式木屋,中间是碎砖铺就的路,一个日本兵在女性管理者的陪同下准备进入房间。旁边的文字说明是:上海杨家宅慰安所,1938年1月建立,日本上海派遣军东兵站司令部管理。
这个杨家宅在上海的何处?里面的“慰安妇”是什么国家的女子?后来这个慰安所怎么样了?这些问题萦绕在我的心头。回到上海,我几经周折找到了位于翔殷路北侧的“杨家宅慰安所”遗址。它是全面抗战爆发后上海第一个由日军直接设立和管理的慰安所,其间的受害者大多数是从朝鲜和中国各地俘虏过来的。
调查越深入,结果越惊人。当年,日军在上海设立的慰安所散见于城中各个角落,至少有172处。其中,位于东宝兴路125弄的“大一沙龙”是世界上存在时间最长的日军慰安所,持续时间从1932年初一直到1945年。
「跟时间赛跑,记录历史、保留证据」
上观新闻:抗战期间,在全国共有多少这样的慰安所?
苏智良:日军在华慰安所分布图,我们已经更新到第10版了。像山东、河南、河北、湖北、江苏、上海一带,都是密密麻麻的据点。这些慰安所遗址,都是由我们团队一个县一个县去调查、实证研究确认的。
具体到慰安所数量,福建是22个,云南是36个,广东是40个,广西是46个,湖南是47个,河南是57个,江苏南京有70个,安徽是71个,海南是92个,山西是116个,台湾是130个,浙江是183个,山东是208个,湖北是295个,加上上海的数字,累计已达1585个。东北等地的数据,我们还在调查中。
一个慰安所里,“慰安妇”多的有300至500人,少的仅1人;“慰安妇”受难的时间短则数周,长则达7年之久。经过30年的努力,我们获得的“慰安妇”受害者个人信息超过400人。
上观新闻:1000多个慰安所中,哪些值得保留?
苏智良:不是说所有的慰安所都要保留,但一些非常重要的据点、非常完整的证据链应该予以保留。我国已在云南龙陵董家沟慰安所旧址、黑龙江孙吴“军人会馆”旧址建立了陈列馆,对武汉积庆里慰安所旧址、广东珠海三灶岛日军慰安所旧址、广西荔浦马岭慰安所旧址等进行了保护。
我们来到波兰奥斯威辛,会受到很强烈的震撼:铁丝网、毒气室、假肢,以及用犹太人头发制作的军毯,没有用完的头发在那里堆成了山。这样的真实感、现场感,让人一看就知道是无可辩驳的证据。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在面对自己曾经遭受的历史伤害时,保留证据的完备程度就是引起世界注意和重视的程度。尤其是作为受害国的民众,我们都不保留证据,难道还能指望加害方不能忘记历史?所以说,我们这30年来所做的一直是在跟时间赛跑,一直是在记录历史、保留证据。
2008年春节,苏智良、陈丽菲来到广西荔浦瑶族老人韦绍兰的家进行调查。
「回忆往事就像死过去一次,非常痛苦」
上观新闻:“慰安妇”问题研究难在哪里?
苏智良:由于“慰安妇”制度具有隐秘性,加之日本刻意销毁证据,留存的文献相对较少,因此以访问者口述印证他人口述、以口述印证文献的方法便显得极为重要。
在独自调查两三年后,为进行系统化、专业化的调查和研究,我在各地聘请了60位调查员,有教授、律师,也有农民。我们的足迹遍及从黑龙江到海南岛的20多个省市。
“慰安妇”的惨烈经历,使幸存者的身心遭受很大创伤。一开始,很多幸存者都不愿意谈及这段经历。因为对她们来说,回忆往事就像死过去一次,非常痛苦。
有一次,我得知上海有一位“慰安妇”幸存者。我特意请人把老人带出来,就是为了避开她的家人、邻里,但她就是不愿意回想。最后,她悄悄地对我说:“事情已过去那么多年了,就让它烂在我的肚子里吧。”
我很理解老人的心情。伤疤一旦揭开,难免会加深她们的痛苦。有的在讲述时会无法控制,号啕大哭。但从历史研究的使命和责任来讲,我们还要继续,也必须继续。
上观新闻:对于这些老人来说,这确实太残忍了。
苏智良:的确如此,所以我很感激那些愿意作证的幸存者。
我们也有很多失败的调查经历,后来才逐步摸索出一些窍门。比如,一定要女性领队,男性最好待在另外一个房间。又如,我们团队有个约定,一般不带记者。还有,我们尽可能在一两次访谈中把所有事情搞清楚,之后再跟老人谈一些开心的事。
在20万被日军蹂躏的中国女性中,万爱花是站出来控诉的第一人。我第一次问她:有什么能够证明您受害?她想了一下说:我第一次被日军抓到据点时才15岁,盖的被子是日本兵从侯大兔家里拿的。当时被子都很罕见,所以印象深刻。逃跑的时候,我把那个被子拿回去,还给了侯大兔。
我们打听了一下,这个侯大爷在40里外。我们就直接开车过去,向侯大爷求证。他说:有这回事。我们就是这样,用多重证据来确凿记录史实。
调查时,我们经常会问这样一个问题:您带了什么东西逃出来?问100个人,基本上都说:命都没了,还拿什么?但前面提到的雷桂英老人,叫养子从床底下取出一个瓶子。东西倒出来一看,是高锰酸钾。这是日军用来给“慰安妇”身体消毒用的。雷桂英老人说:“我当时就想把这个东西带出来,为的就是留下证据给大家看!”
「宽容是一种美德,姑息却是一种错误」
上观新闻:记录这段历史,到底有什么用?
苏智良:有一次,外交部门组织与日本右翼团体对话。轮到我发言时,我把日本陆军省的文件拿出来,文件上白纸黑字:要建400个慰安所,要“征募”妇女。在日本利用国家力量推行“慰安妇”制度的铁证面前,日方的态度和立场不得不有所改变。这就是我们的工作的意义。
宽容是一种美德,姑息却是一种错误。我们要用历史事实告诉他们,日本在战争时候对中国人民、对亚洲人民犯下了不可推卸的罪行,必须真诚忏悔,更不能颠倒黑白。
这几年,我也到一些中学给学生讲课。我讲了一些受害者的个案,讲到万爱花想方设法逃出日军魔爪,结果三次被抓回炮楼;讲到韦绍兰千辛万苦逃回家后却发觉怀孕了,最终生下孩子,忍辱负重一辈子……听讲的很多孩子都流泪了。我对他们说,希望你们一辈子铭记。
20世纪80年代,苏智良在华东师范大学求学。
上观新闻:您希望年轻人从中牢记什么?
苏智良:历史虽然已经过去了,但我们要牢记它。这么做并非带着仇恨,而是认清真相,吸取教训,走向未来。
作为大学老师,我很欣喜地看到年轻一代在获取和学习信息的能力上超越老一辈。但在人生观上如何克服可能存在的个人主义、主观主义,在世界观上如何全面而客观地看待中国和世界,在价值观上如何实现个人价值和社会价值的统一,可能还需要好好在实践中磨炼一番。同时,在历史面前,还要多几分敬畏之心。
就“慰安妇”问题研究来说,我也希望能有更多年轻人来参与。“慰安妇”问题是一个综合性问题,不仅需要历史学者的视角,社会学、心理学、法学、地理学等研究者的参与也同样重要。
面向未来,我们还要梳理整合中英韩日各种文字的“慰安妇”文字和口述资料,编辑资料集和影像资料,考察战后国际社会和日本政府对“慰安妇”问题的态度演变,以文献与口述材料互证的方式,更加深刻全面地揭露这一战争犯罪的实质与影响,为下一代留下更有价值的研究。
苏智良上海师范大学教授,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基地上海师范大学都市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兼任中国城市史研究会副会长、中国现代人物研究委员会主任、中国“慰安妇”问题研究中心主任。